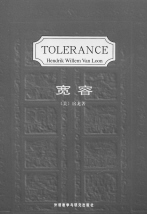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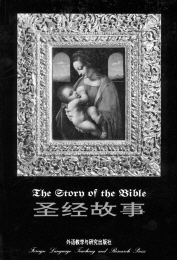
人类历史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演化的?人与历史关系如何?人是如何去创造历史的?人何以要去认识历史?
对上述疑问,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思想家普遍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无论是从生产关系变迁的角度去理会社会发展,还是从生产力更替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变迁,抑或从现代化论者论述人类文明变迁……无不如此。而荷兰裔美籍历史学家房龙(HendrikvanLoon,1882~1946)则别出心裁,从社会或人是否宽容的角度来体会、感悟、理解西方历史的变迁。“宽容”与“不宽容”,正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谁成为时代的中心或哪一个成为边缘,时代的历史风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因而,用这种方法理解人类文明,人类历史的变迁无疑是处在无序与有序不断交替的状态。
作为一个概念,“宽容”远不止是人的一种心态、性情、品行等个人行为。房龙先生写作时期所通行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本(第26卷第1052页)这样定义“宽容”(toleranc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这个公共定义,80年来基本上没改变。在21世纪可能更不会改变,相反会更有魅力。不过,这个抽象的说法,在房龙个人视野中却是人类文明是否顺利更替的生动描述,而不是一种准确的定义。
但是,房龙先生却不是根据这个概念来裁剪历史。在西方广为人知的《宽容》(1925)中,作者房龙先生不是直接赞美符合宽容标准的历史过程、否定或批评不宽容的历史现象,而是抓住人类文明变迁历程中“宽容”与“不宽容”所呈现出的各种形态,来描述社会发展何以如此的变迁规律。在他看来,人类身上普遍存在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三种不宽容现象:“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是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例如不同地区或时代之间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是不尽相同的,然而人或动物的生活习惯所养成的惰性、生活经验的有限性,使之不能互相容忍,由此使得父母对子女行为摇头叹息、大部分人荒唐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习俗使之不思进取、守旧)、抱有新思想的人往往成为人类的敌人,人人都有可能遭受这种不宽容之罪,“历史上许多人曾因此背井离乡、如今一些渺无人烟之地也因此意外出现居民点”,不过这种宽容相对而言还是无害的。“第二种不宽容来自无知者,仅仅因为对事物无知这种人就会成为危险人物,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低下而辩解那就更为可怕,这种人永远自我标榜正确、始终不能理解和谅解与自己不一致的他人,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会反对并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若是有人批评这是不宽容的行为,他们反而沾沾自喜,这种不宽容的危害更为严重”。“第三种不宽容是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是嫉妒的一种表现”,这是最为严重的现象。不过,“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人类许多黑暗岁月,或者在人类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这三种情况常常是并举的。由此造成历史进步的艰难。
不仅如此,在房龙看来,不宽容还有个人和社会之分,其中个人的不宽容“是一个讨厌的东西,导致群体内部产生极大的不愉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端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没有有效控制的手段);“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做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但是官方的不宽容则不然,它“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者于死地,也不做任何返回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旨意”。房龙先生特别憎恶、恐惧和担忧的是官方的、群体的、社会性的不宽容。
既然“不宽容”现象是如此繁多、存在的状态如此普遍,那么在人类文明中它最早是如何产生的呢?不宽容与宽容之间关系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房龙先生《宽容·序言》。在短小篇幅中,他是如此别开生面地描绘“不宽容”产生时的情形:在文明到来之前的时代,人生活在物质贫乏、生存空间封闭而狭小的“无知山谷”里,人们靠一代代人的经验积累而建立生活的规则、理念,因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老人因其经验丰富而成为权威,老人讲故事不仅是他们消遣老年时光的方式,而且是给年轻人传授部族精神、建立部落权威和律法的途径。多少年来,没有人打破这种秩序,“人们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过着幸福的生活”。长此以往,就导致处在愚昧、封闭和保守环境中的人与其相应的全部生活之间不断恶性循环。然而,人类中总是有不畏惧螃蟹、不相信“螃蟹是不能吃”的古训、敢于吃螃蟹的勇者。在房龙先生形象化的叙述中,这种人便是敢于走出部落世界的年轻人,他独自去危险的岩石高墙之外探险,而且他获得了成功:活着回来了,并发现山那一边的世界很精彩。他活着回来这个事实,却证明了一代代老人智慧的荒谬、千古不变的古训是谎言,因为人们一直不怀疑老人说的“山那边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可是,“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冷漠”,老人的意见即律法,“他违背了守旧老人的意愿,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守旧老人是执法者”。触犯这种习惯法的人,无论他的行为多么高尚正直、为高尚付出了多么重的代价、他的行动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人们是不会以理解、容忍和同情之类心态对待他的,他不会幸运地被赦免审判,或者说无所不在的习惯法使他难逃法网。于是,在“法庭”上他说的内容越真实、把外面世界描绘得越精彩、辩护的态度越坚决,他就越引起公愤、越没有可能逃脱最残酷的惩罚(“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人们杀死了这个漫游者”)。不过,他作为勇者和真理的见证者,对在缺乏宽容精神语境中的个人安危也是无所顾忌的,尽管这种气魄在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威力来。房龙先生进而生动地描述了不宽容的代价:自然规律使这个孤陋的世界遭受了自然灾难,生活规律却使这里的居民在灾难面前没有自我拯救能力,只是因为人们求生存的自然本能才去质疑老人意志的法律性、真理性,在付出许许多多牺牲之后,人们重新走向先驱者冒着生命危险走过、在法庭上辩护过、为他们指点过的通道。这种不宽容的悲剧,“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了”,而房龙先生去世大半个世纪了,这种愿望依旧没有实现,因为不宽容“不过是人们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而且“只要不宽容是我们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就是犯罪”。
在这种基础上,房龙先生理会了“宽容是什么”:宽容的实质是群体或公众或社会是否许可异端,“宽容就如同自由”,宽容作为人自身的特质之一不具有强大力量去规范人类历史沿着进化论方向发展。特别是,要做到宽容是极其困难的:“宽容”不能作为专业问题来研究,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宽容只是一种副产品,人们可以美言宽容、对宽容感兴趣,但不会为宽容奋斗。即便为宽容而战的人,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相信自己正确,同时却不原谅他人的信仰。在这种“不宽容”与“宽容”理念中,房龙阅读历史时就发现:在古希腊联邦,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能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于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创造要能够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的自由思想,因其宽容理念预设着社会容许任何思想自由存在,因而当局害怕他,在他70岁的时候还判他死刑;古罗马人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遵从当局指定的为数不多的规则,就可以自由的信仰任何上帝,“罗马的和平”有赖于实践“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之原则,500年历史中一直宽容对待宗教,最大限度的减少摩擦,然而要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又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这正好与其传统的自由政策背道而驰,于是帝国最终分崩离析;中世纪历史的主流是靠教会来推动的,教会借助物质上的限制和精神上的束缚使民众臣服,禁止所有自由思想,作为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们把柏拉图等所有思想家建立追求正义的理想国的渴望歪曲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教会的战士,他们要维持生存就必须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信仰上帝之外的科学行为表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18世纪是保卫宽容的时代,但是最终结果是以一种不宽容推翻另一种不宽容……在房龙眼中,既然宽容是如此微弱,而不宽容又是人性中极大的弱点,那么希冀它的到来“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21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强大辐射力,不断改变“中心”与“边缘”位置,如此一来“不宽容”能否更快一些转化为“宽容”呢?例如,东方对西方文明的宽容或者西方改变了对东方文化的漠视,体制与体制之间不再对抗或体制内部成员的相互依赖,诸如此类现象能得到更迅速的实现。
正因为房龙先生这种特殊而自由地阅读历史的经历,使他有可能以崭新的视角重构历史。在此书中,房龙果然出手不凡,找到了是否“宽容”的通道进入了人类文明深处。如此独特书写历史的做法,不仅打破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进步的乌托邦幻想,而且进一步打开了人们认识历史变迁的思维空间,提前揭示了后现代景观下的文明形态。
